
“新月派”诗人、古文字专家陈梦家。(网路图片)
【大纪元2017年03月03日讯】(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)这是一位与汉字有着不解之缘的乱世才子。曾经的他浪漫潇洒,以笔墨作针线、汉字作珠玉,串连成含蓄优美的“新月派”诗歌;后来的他严谨治学,钻进浩如烟海的古籍世界,探寻枯涩艰深的古文字之谜。
再后来,他为之耗费无数心血的中国字,面临消亡之劫。他出于一个炎黄子孙捍卫民族文化的使命感,四处奔走向当局政府呼吁。因文字成名的他,却因文字获罪。在历经一次次批判与打压的折磨后,他不堪受辱,愤然了结性命,与博大精深的传统汉字,一同亡于当权者之手。
今天的中国大陆,几乎看不到传统汉字——正体字的踪迹,也鲜有人会提起国学大师——陈梦家的名字。

1947年,陈梦家(左)、赵梦蕤(中)夫妇与家人在美国合影。(网路图片)
长衫落拓美少年
陈梦家于1911年出生于一个神学家庭,在中式传统教育和西方宗教氛围中度过童年,对中国诗歌有浓厚兴趣。1927年,陈梦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法律系,虽然后来取得律师执照,却没当过一天律师。以新诗为媒,他在学校里结识大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,并长期与他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,其诗歌水平也随之突飞猛进。
“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,不想这小生命,向着太阳发笑,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,他的欢喜,他的诗,在风前轻摇。”(陈梦家《一朵野花》)
“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,小星点亮我的桅杆,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,新月张开一片风帆。”(陈梦家《摇船夜歌》)
诗人穆木天曾评价陈诗“好如一片秋空,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”。受两位大诗人的影响,陈梦家的作品兼具声律谨严之韵和轻俏流丽之美,他也因此成为“新月诗派”的一员主将。
1931年,陈梦家年方弱冠,便出版第一部诗集《梦家诗集》,同年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,编选新月派代表作《新月诗选》。花了大约一个月时间,陈梦家不辱使命,甄选18位诗人的共计80首新诗编成诗集,呈现“新月派”前、后期在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上的流变。
在众人眼中,少年得志的陈梦家是个洒脱不羁的文艺家。梁实秋说他是“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”,钱穆说他“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”。然而他的生活轨迹很快发生逆转。
后来,陈梦家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专业,很快又转攻古文字学——只因他对中国上古神秘的宗教文化抱有极大的好奇心。他把所有精力投注于古文字学和古史学方面,仅1936年便发表《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》《商代的神话与巫术》等7篇论文。
在燕大读书,陈梦家收获的不仅仅是学业,还有人生。他与才女校花赵萝蕤相识,相同的神学家庭背景和文学修养,让两人一见如故。1936年1月,他们在校长办公室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。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这对璧人被迫迁离北京,辗转于长沙、香港、昆明等地,在西南联大暂时栖身。直至1944年,经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和清华教授金岳霖介绍,陈梦家越洋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学,随行的赵萝蕤也在该校攻读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生课程。

陈梦家、赵萝蕤夫妇(前排)与家人合影。(网路图片)
一身诗意付金石
虽然在美国教授文学,陈梦家已逐渐从文人向古文字专家转变。执教期间,他致力于收集、汇整流散于美国的古代铜器,几乎走访美国所有藏有铜器的人家、博物馆乃至古董商铺。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学力,编纂殷周铜器集录,为研究中国铜器留下宝贵材料。
1947年,陈梦家怀着报国理想回国,在清华中文系执教,同时坚持古文字学、西周铜器等文字学与史学研究。次年,赵萝蕤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国团聚,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。这对乱世中的学者夫妻暂时过上稳定平静的生活。
然而没过几年,中共占领中国大陆,陈梦家夫妇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即将面临中国最黑暗邪恶的时期。
1951年,中共为“抗美援朝”造势,发动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”,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校园,要求学校停课搞“运动”,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改造和检讨,清算“美帝文化侵略”,而且要“人人过关”。陈梦家因个人的浪漫派诗风和出国背景难逃被改造的命运。
1951到1952年,陈梦家多次在学校大会上作检讨,表示自己因接受西式教育而无法融入“新社会”。他愿与过去的思想和观念“一刀两断”,并接受“新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”。而妻子赵萝蕤作为西语系教授,也要被迫参加各种会议,检讨“资产阶级思想”及“重业务、轻政治”的教学倾向。
陈梦家一方面配合运动作检讨,一方面也因无法理解这种运动,私下里评议时弊。一天,校园的大喇叭广播一项通知,要求全体师生参加“集体工间操”。陈梦家听到后说:“这是‘1984’来了。这么快。”《1894》是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,预言集权社会的情景,陈梦家借此含蓄地讥评中共体制。
1952年,运动刚结束,中共又在全国展开高校的院系调整,陈梦家被分配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,妻子赵萝蕤转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。
“诗家不幸史家幸。”在考古所的最初几年,陈梦家的生活相对平静,在考古方面的学术研究建树颇丰。他借鉴西方学术规范,先后完成《殷墟卜辞综述》《西周铜器断代》《尚书通论》等专著,成为名副其实的古文字、考古学大师。1956年,陈梦家还用丰厚的稿费购置一套四合院,每天在家工作超过10个小时。他还热衷于购置明清家具,在家中悉心收藏、展示,被朋友戏称“比博物馆还博物馆”。
他却从此搁置诗笔,鲜有文学创作。严苛的政治环境,是扼杀诗魂与灵感的最大杀手,陈梦家的浪漫诗风已被主流文学抛弃,他只得选择缄口不言,把所有精力灌注到遥远的古代世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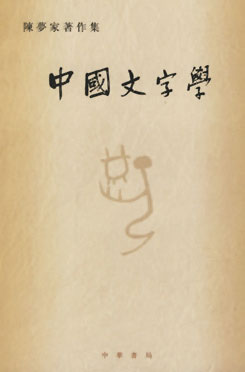
陈梦家著作《中国文字学》(网路图片)
不知言路成绝路
1956年,中共在大陆实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政策,次年发出《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》,鼓励“大鸣大放”,制造出政治气氛变暖的假象。陈梦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,以为中共真心纳谏,欲将多年前想提而不敢提的意见真诚吐露。
1935年,中华民国曾公布300多个简体字表,推广汉字改革。因遭到社会人士反对,国民政府便于次年下令停止推行。一心毁灭中国文化的中共,从成立之初就逆势而行,逐步毁灭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汉字。中共先将汉字歪曲成“横亘在群众和新文化之间的‘长城’”,又在1930年编造一套适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统。1936年,毛泽东更对记者公开表示,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
1949年,中共全面控制大陆后,成立“中国文字改革协会”,正式着手汉字简化工作。中国语言学家在中共的指示下,先后提出千百种改革方案,最终决定使用简化汉字作为过渡,逐渐实现字母化。
作为用汉字写作并探寻古文字脉络的文人,陈梦家深知传统汉字对中国人的重大意义。汉字如果被废除,将真正成为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障碍,中华文化的传承也随之被切断。这对拥有五千年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来说,无疑是最大的损失。
之前,陈梦家慑于运动的压力,有口难言;到了“鸣放”时期,他便积极地向中共发起呼吁。1957年2月,他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略论文字学》,批评汉字简化方案。3月起,他参加文字改革座谈会,发表演讲,表达不赞成简化汉字的看法:“如果废除汉字,改用拼音文字,不免会引起天下大乱。”
5月17日,陈梦家继续为保护正体字发声,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文章《慎重一点“改革”汉字》。他却不知道,就在两天前,毛泽东写下《事情正在起变化》,发出打击右派的信号。这样,陈梦家关于反对汉字改革的言论,成为他在“反右斗争”中被批判的最大证据。
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后,学术活动完全停止,在单位里遭到“降薪停职使用”的处罚,在社会上更要忍受一众学者的联合批判。从此,等待他的是参加不完的批斗会、做不完的自我检讨。陈梦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,变得情绪低落,身形消瘦;赵萝蕤因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灾祸,患上精神分裂症。偏偏这时,在1958年12月,陈梦家被下放到河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,一代古文字专家只能做些种田、踩水车之类的农活。
直到1960年,陈梦家才重新回考古所,受副所长、他的朋友夏鼐照顾,调往兰州整理汉简,成为他不幸生活的一次大幸。在那里,陈梦家专注考古研究,以超乎寻常的才华完成《武威汉简》《汉简缀述》两书。两年后,他又回到考古所。虽然后来摘掉“右派”帽子,但是遭受过两次运动迫害的他仍然心有余悸,遂一心扑在考古研究中。

陈梦家、赵萝蕤夫妇合影(网路图片)
两度求死浩劫中
文革的爆发,堵死了他的最后一条出路。1966年8月,陈梦家第三次被中共“批斗”,也是最悲惨的一次,直接导致他的自杀悲剧。
陈梦家在文革中被划为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,重新被揪出批判、斗争。作为考古所的领导,夏鼐目睹陈梦家遭受迫害的经历,并在日记中留下第一手资料。考古所成立了监督小组,每天强制陈梦家与其他“反动分子”上午劳动,下午写检查。烈日当头时,他被迫长时间跪在院子里,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,甚至吐口水。
他的四合院被红卫兵查抄,家中藏书一扫而空,住所被他人占用,陈梦家夫妇只能住进一间车库改造的破屋。期间,赵萝蕤两次发病,都因为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而去无法送医。
8月23日,红卫兵闯入考古所,揪斗陈梦家;24日继续批斗,还给他戴上“流氓诗人”的纸帽,并勒令他写检查。陈梦家捱过了一天的批斗,来到一位朋友家。屈辱与绝望带来的悲愤之情一瞬间爆发,他放声呐喊:“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!”谁知他被考古所的“造反派”一路跟踪。在朋友家中,他们继续狠狠批斗,强行按着他下跪,进行又一轮辱骂和毒打。最后,陈梦家又被押回考古所。
可怕的“红八月”,正是红卫兵造反运动最为血腥的时期。24日当晚,考古所附近的东厂胡同,至少有6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。有人回忆,“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”,“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”。被关在单位的陈梦家,应该也听到了一声声的拷打与惨叫。那一晚,他悄悄写下遗书,吞下大量安眠药。
因药量不足以致死,陈梦家被送往医院抢救过来。然而大难不死,未必有后福,第二天他的家里就贴满了大字报,前去探望的弟弟陈梦熊还被红卫兵拦住毒打一顿。陈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就被轰出来,身边多了几个看管他的年轻同事。9月2日,他趁众人不注意,选择更直接的自杀方式——自缢身亡。而3天后,考古所召开“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”,为这位终年55岁的饱学之士“送行”。
他卸下了一身重担,此后生活的悲痛与苦难都由赵萝蕤一人承担。她在文革之后继续执教,耗时12年时间完成《草叶集》全译本,震撼世界学术界,一举获得芝加哥大学“专业成绩奖”。然而她直到1998年去世,都不提过去的伤痛,更不提丈夫的名字。
陈梦家在著名诗歌《铁马的歌》中说:“没有忧愁,也没有欢欣;我总是古旧,总是清新。……也许有天 上帝叫我静,我飞上云边,变一颗星。”他仿佛预见受难而死的结局,便想让自己变成寒夜孤星,永远无声地注视着中国大地。
这是一位与神结缘的诗人、和文字对话的学者,原本与政治无涉,却在三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打垮,直至殒命。中共妄图用政治掌控传统文化与文化精英,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文化的衰败和大师时代的消亡。
参考资料:
1.王友琴,《文革受难者》,香港《开发》杂志出版社,2004年。
2.刘宜庆,《陈梦家和赵萝蕤的葳蕤人生》,《名人传记(上半月)》,2010年第10期。
3.汤志辉,《“运动”中的陈梦家》,《粤海风》,2015年第3期。 #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